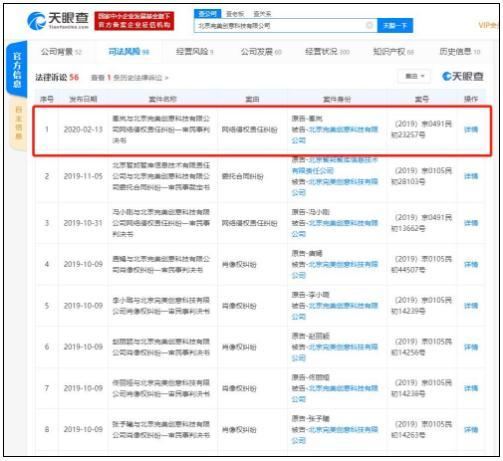导演处女作电影 《六欲天》上映 是导演 也是主演
祖峰:人过四十,走出抑“欲”
导演处女作电影 《六欲天》上映


准确地说,祖峰四十五了。
他坐在沙发上,身体比蜷缩要直一些,比挺直又弯一些,像是一个拉长的字母C,一直保持了一个多小时。
始终的,还有他的双手,不停地鼓捣着,要么是指甲,要么是衣服上的一根带子。
“你很紧张吗?为什么手总有这样的小动作?”我问。
“不紧张啊。”他脱口而出却声音不大,“我平常聊天也这样。”
抑郁吗?
10月31日晚上7点10分,苏宁影城的大厅,《六欲天》的海报四处可见,影城的员工或在为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工作而忙碌,或在柜台不时接待着前来询问影片的顾客,尽管大部分人是到影城所在商场吃饭的,有的嘴里还咀嚼着一个包子,或者一个煎饼。
距离这部影片上映,不到24个小时了。
休息室里,这部影片的导演,也是主演,祖峰,还在等待化妆师的最后一道工序:打摩斯。“我现在净是白头发,都在头顶上。”短发的祖峰一乐,皱纹便在额头与眼角间“渐隐渐现”起来。
除了发型,休息室里的祖峰与电影《六欲天》里的祖峰形象没有太大反差,甚至衣着的风格。真的区别在于眼睛——电影外的祖峰,虽然戴着眼镜,但是眼睛镇定有神;而影片里的祖峰,眼睛迷离无神。
《六欲天》是祖峰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长沙的故事:因前女友自杀而患上抑郁症的警察阿斌,在调查一起刑事案中,根据被害者姐姐李雪的梦境,分别在树下和江边找到部分碎尸。警察阿斌的上司李磊怀疑李雪和这起案件有密切的关系。案件侦破中,阿斌发现李雪和他一样,都有段无法坦言和直面的过去,两人渐渐理解彼此,相互帮助。
影片虽然以一起刑事案件为依托,但真正表现的却是一种深陷于抑郁却又试图摆脱它的生活状态。问题是,祖峰如何去把握那种抑郁状态呢,不仅仅是阿斌这个剧中人,也包括影片整体的风格。
“你抑郁过吗?”我问。
嫉妒吗?
“你七几的?”祖峰问我。
继而,他说:“我七四的,我刚到四十的那几年,很抑郁。”
“一般人的压力都会有,虽然可能我的经济方面会好一些,但生活、家庭、责任等等,各个方面都还是会感受到一种压力。”祖峰说,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职业的评定”。
“那些年是这个行业最不好的时候。”祖峰声音很轻,但看了我一眼,“现在都说演员的春天来了,但三四年前,包括四五年前并不是这样的。”
在祖峰看来,那是一个“特别唯流量的时代”,很多的制作单位看的是“漂亮的面孔”,似乎演技这件事无关紧要,“这就让我感觉上不是太舒服。”
“是因为看到别人很‘红’所产生的一种嫉妒吗?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圈子充满了嫉妒。”我问。
“嗯……也不是。”祖峰语速没有变化,“只是觉得互联网蓬勃发展,有大批的资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把这个行业搅乱了。”
“你说这话不怕把‘大量资本’得罪了?”我问。
“那怎么办呢,你说。”祖峰说,“你想若干年以前,所有的影视公司都在说上市,然后确实也有很多影视公司上市了。但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业绩给他们带来的压力会造成产量增多了,精品量下降了。我是觉得影视产业它是一个创意产业,不是说给你两年的时间你就能做出一个东西来,有的可能得孵化很长时间,它真的可能得需要灵感。所以很多项目就赶紧运作,赶紧回收(成本)。包括IP炒得也很热,因为快嘛。”
“整个行业的气氛是很蓬勃。”祖峰继续,“但是你能感觉出来泡沫已经很膨胀了。”
“虚胖囊肿?”我说。
“对。”祖峰说,“你想如果资本得不到快速变现的那个结果,它会很快地离开这个行业的。那剩下的我们这些吭哧吭哧在这个行业里工作的人怎么办啊?”
没人找你吗?
“人很难在面对那样的热钱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思考,你为什么会思考这些,因为没人找你吗?”我问。
“也不是,很多人找我,但项目不成熟。”祖峰举了一个例子。一家公司找他拍片,剧本计划是四十集,已经写了两年,写了十几集,声称马上就要开拍了。“这事儿不能干啊。”祖峰的语速快了。
“你说这剧本他两年都没写完。开拍剩下这俩月他能把后二十集写完吗?这一定会造成质量问题的。”祖峰解释他为什么拒绝。 “也不是我一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行业里很多人也会这样想。这样仓促的剧本,会有很多硬伤,故事逻辑、情感逻辑……你怎么去扮演这个人物呢?你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你一睁开眼睛,就看到那个剧本,在那个创作环境里,其实很痛苦的。”祖峰说。
会吗?
步入四十岁的祖峰不得不去思考“这个如何更长久”的问题。思虑过多,他陷入了情绪低落、没有活力的抑郁状态,“不愿意社交,好比朋友说谁那儿有个局什么的,打电话……完全不愿意去。”
祖峰希望用兴趣爱好摆脱这样的状态,例如和一群编剧和大学同学踢踢球、打打网球,最主要的是抄书写字,“我从大学就开始写书法,这些年更多了一些。”在那段特别难熬的“情绪”日子里,他每天上午都用来干这件事,“抄书的过程也是读书的过程,大学的时候虽然也读书,但是太少了。”
那段时间里,拒绝社交的他,面对找上门的“活”,变得特别地挑剔,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确实人家找上来,你拒绝了,人家就不再找你了。”祖峰说。其实,演《潜伏》成名后,祖峰原本会有更多大“红”的机会,但他提到的却只有2014年拍的《北平无战事》,这一部片子而已。
祖峰说他也一直拒绝宣传自己。除了配合片方做的必须的作品宣传以外,他一直拒绝关于他个人的专访或者宣传。“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有点像‘吹牛’。”说了一句脏口以后,祖峰又恢复了平静,“就像经纪公司包装一个演员,感觉像把这个产品说得特别好,有销路,我就觉得特别的那个……”
“特别的不自然。”祖峰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其实“不自然”的不止祖峰,他提起了好友周迅。在一个剧组里,他和周迅也聊起了关于“包装”的事情。“周迅说她也不喜欢‘包装’自己。我们可能还是那种比较老范儿的人。总觉得只要你有本事就没有问题,是金子总能发光吧。”他又笑了一下。
“现在感觉这观点可能不行了。” 他干笑了几下。
祖峰说自己也一直在慢慢调整自己的这种认识和心态,“其实,还是有很多关心你的人需要知道你,让别人知道你并不是坏事。”
但是他话锋又一转:“现在大家好像商业化思维太重。我是觉得做事还得踏踏实实地做专业相关的事,但有的时候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个好像就走歪了。”
“会吗?”他看了我一眼。
找到门了吗?
这样的一段“抑郁”经历让祖峰看《六欲天》剧本时有了一种感同身受,但这只是他喜欢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剧本里所体现的关于“孤独”的命题,关于如何“自我救赎”的探寻……这些都是他决定参与这部影片的原因。
起初他只是演这部电影,但想完整地去传达这个故事的含义,并不是演员这个工作所能完成的。制片方鼓励他做导演,可是他犹豫了。因为导演工作太麻烦,他不得不去独立地面对各个主创部门,各位演员,还有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包括和制片部门研究拍摄进度,甚至于天气情况也不得不去考虑,“太繁琐了,演员多单纯”。
制片人对他说不用去考虑创作以外的事情,那些事情由他来解决。于是,祖峰开始琢磨导演这件事了。2017年在一个剧组拍电视剧的时候,他正好有空闲可以冷静地去分析剧本,大概地想了几场戏,大概地能够找到一个方向。下了剧组后,他对制片人说“好,我决定了自己拍了。”
从拒绝到接受,祖峰的转变并没有像任何一部电影那样必须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故事或者情节,但确实有一道打通思想的“门”。“之前电影怎么拍,感觉始终没有一个门路。后来找到这个门了,就敢答应了。”祖峰说。
与电影对话的门找到了,但与摄制组人员沟通的门找到了吗?
“我特别害怕现场气氛特紧张的那种。”祖峰说他不喜欢那种在现场骂工作人员,甚至连摄影师都骂的导演。在他看来,这样的导演会让紧张的情绪像一种波似的蔓延着,影响每一个人的工作,从演员到摄影师。
祖峰并没有被导演骂过,但遇到自己实在看不下去的情况时,他会上前去劝一下:“哎呀,不要把这事弄那么严重”,另外他心里头也会偷偷地想:“下回别再跟这导演合作了……”
“这要真遇到艺谋导演、凯歌导演这样的大导演可怎么办啊?”我笑问。
“那怎么办,那就不做了呗。”祖峰做了一个怪表情,然后幽幽地说,“其实,像他们这种真有本事的、好的导演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就希望现场不能有这样的氛围,我希望给每个人一种安全感。”在现场,他跟每一个人沟通的时候,说话永远保持着柔和的、低沉的语调,就像现在面对专访的时候。
他说自己找到了沟通的法门——“换位思考”。
欲望呢?
尽管名字叫《六欲天》,但是在燥热的六月里,却看不到一场“激情”戏,甚至吻戏,只是偶尔的能够看到一条废弃的胳膊,刺激一下观众的神经。
“原本有激情戏的安排,但后来给剪掉了。”祖峰说围绕我们的欲望方方面面,求生欲、食欲……这些都是欲望,“不光是情欲”。
没有直接展现情欲的桥段,也没有血腥的暴力场面,甚至于没有一眼便可看穿的风格化镜头,在这样一部“无欲”的影片背后,是祖峰回归传统电影表达方式的尝试。他希望用冷静、常规的镜头语言,最大地发挥演员的表演,从而将观众带入一个能够冷静思考的电影叙事世界之中。
他希望在镜头内部,观众可以看到两种生活态度,一种是属于他所演的主人公阿斌的那种,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里;还有一种是像阿斌的同事伟哥那样,活在当下,当断即断,不会沉浸在痛苦之中,“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也挺好的”。
“不是‘也挺好的’。”祖峰调整了说法,“就是挺好的。”